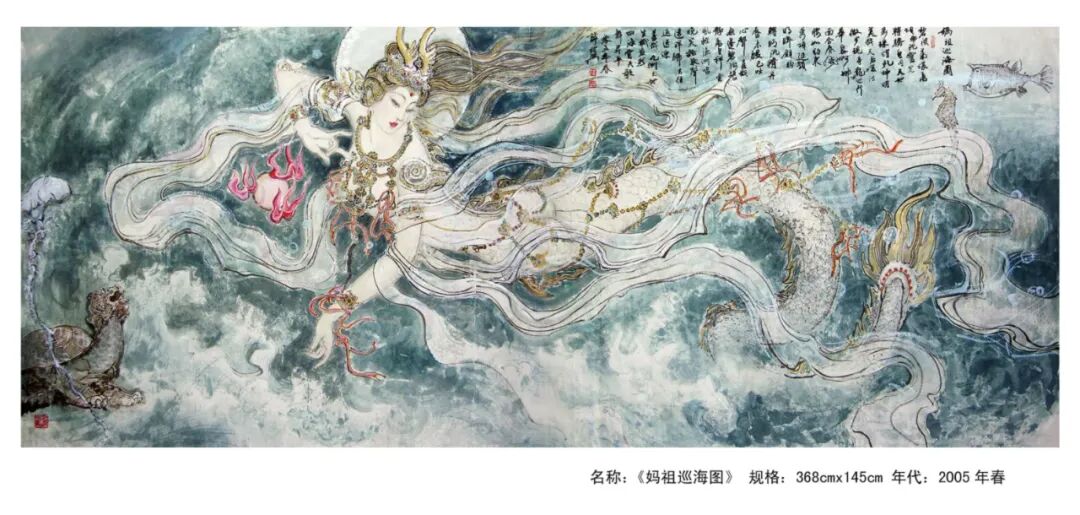范妮:只有心存执念,才能走到最后
10月30日晚,在北京音乐厅,指挥家范妮回到了她的老本行——打击乐的舞台,和她的朋友曲大卫、邵哈哈以及学生们一起为京城乐迷带来一场热烈、开心、有趣而又高级的打击乐音乐会。前几天,范妮以指挥家的身份挥棒北京民族乐团上演了一出“国乐的摇摆”音乐会,当晚她出人意料的客串了一把打击乐家,带着现场观众可劲儿的嗨了一把。这一晚,没有指挥家范妮,只有打击乐家范妮。舞台上,她不仅尽情地展示了自己眼花缭乱的打击乐技巧,同时更是和自己的伙伴们用各种可能展现了打击乐的独特魅力和魔力。这是一台难得的音乐会,因为这几年打击乐家范妮已经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指挥台上,可能今后这样的音乐会都会越来越少了。人如果将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必须专心和执着。就像范妮对自己父母说的那句话:“做人不能什么都想要。”从打击乐家到指挥家,未来范妮还有可能去做更多的人生尝试,指挥家对她来说可能也是个过渡。不过,她说:“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心存执念,有执念才能走到最后。”

高级而又有趣的打击乐音乐会
这一晚的北京音乐厅,精彩场面不断,掌声与喝彩声也是此起彼伏。一开场,打击乐家们就将现场气氛烘托起一个小高潮,范妮和她的伙伴们拿着各种乐器敲敲打打的出场,用她的话说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为大家带来一点温暖的气氛。和所有的打击乐音乐会一样,常常是放着各种型号的马林巴、颤音琴以及各种不同形状不同音色的鼓,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的乐器。当晚,范妮除了担任主奏打击乐家,还是导赏嘉宾,她一样一样的跟大家介绍每件乐器的名字、音色、发音原理以及演奏技巧,比如说颤音琴和马林巴的区别等等。




范妮率先带来两首尼尔·罗萨若创作的颤音琴作品《弗雷德》和《欢迎》,她手中上下翻飞的琴槌不断地击打在琴片上,清脆有如山泉叮咚的乐声令人心旷神怡。打击乐家们变换着各种“阵型”,根据每一首曲子将各种乐器不同的组合在一起。上半场最过瘾的环节当属作曲家、钢琴家曲大卫与范妮的演奏的齐克·科瑞亚的《阿曼多的伦巴》,在欢快自由的节奏中,两位演奏家心有灵犀的配合令人叫绝。有趣的是,两人在演奏过程中互换身份,范妮意外地坐在钢琴旁演奏,而曲大卫则操起了琴槌敲起了颤音琴,两位音乐家有趣的互动既显示了彼此心灵相通的默契,又展示了各自精湛的演奏技巧,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下半场开场曲,范妮手拿沙槌在音响的配合下,演奏了一首将电子乐和打击乐结合在一起的作品《沸腾》,显示了这位打击乐家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舞台中央,只有范妮一个人,继而精心闭目轻摇沙槌,继而以“无影手”般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用范妮的话说,这是整场演出她最累的一首曲目。


马林巴曲《小祈祷》是一首销魂的乐曲,范妮将琴槌轻缓的在琴片上滚动击打,将原本一个个的音符连成美妙的不间断的曲线,静静地演奏如同演奏家心中哼唱出来的一首妙不可言的赞美诗。


最欢乐的互动发生在最后,范妮从外地专门买来很多用来打节奏的沙蛋,中场休息进场时每位观众发了一枚,尤其是小观众可是开心得不得了。在范妮的示范和指挥下,全场观众挥动手中的沙蛋和台上的打击乐家一起在节奏中一同完成了这首热闹欢快的终曲,在极度快速的的节奏中和范妮的奋力一挥中音乐戛然而止,全场掌声雷动。
指挥家重回打击乐舞台的感觉
现在几乎是专职指挥家的范妮已经很少出现在打击乐舞台上了,这次临时的“重操旧业”玩儿了把打击乐,感觉与以前不一样了。她说,平时指挥一场音乐会不用什么人操心,但是演奏一台音乐会所有人都跟一块受累,“指挥的准备工作是在演出的前面,比如说排练前排练中你要准备,但是真正演出的时候其实比较放松,因为你都排好了。但是演奏就不同,尤其是我们这种满台的音乐会,今天我一早就在这儿了,你要弄一天细节,最后还是要再演出,这个过程需要一口仙气吊着才行。”还有一个变化,她说:“指挥是一个看全局的人,这次音乐会排练的时候,我经常在非常混错乱嘈杂里面听出错音,这在以前可能不会注意这些事。原先可能我能忍,现在不能忍。”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打击乐家转行做指挥的比较多,而范妮笑着反问,为什么不问钢琴家转指挥或者其他乐手转指挥,为什么专门问打击乐转指挥?说归说,范妮认为,这里面有个比较学术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节奏感,打击乐人确实掌握的会比其他的乐手比较全面,对节拍比较有感觉也比较准确,比如说我像我比较强迫症,经常要求自己卡到特别准的节拍。虽然指挥引领律动是最主要的工作,但一定要打好拍子。另外,我和很多打击乐手一样不看分谱而是总谱,我要知道我的身边是谁,要知道其他乐手都在做什么,我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打击乐家范妮为啥去当了指挥
年轻的范妮从艺以来在国内外屡获大奖,一路顺风顺水,大家都以为这位年轻姑娘会在打击乐的舞台上越走越远。后来,她出人意料的站在了指挥台上,几年来她与德国莱比锡交响管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等众多国内外乐团合作,成为国内最活跃的青年指挥家之一。她不仅指挥西洋的交响乐团,也指挥民乐团。在准备每一场音乐会的时候,自己都会做足很多功课,不管是西洋的还是民族音乐的交响曲,她都会画曲子的结构,她要清楚地了解乐队中每个乐手坐在哪儿。她说:“尤其是指挥民乐的这一瞬间,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切换到在民乐团指挥的思维。比如说前些日子,前一天是德沃夏克,第二天是民乐,这种情况我自己必须强制性切换过来,因为这是职业。”

曾经有人这样问她:“你为什么学指挥?做打击乐家不好吗?”范妮回答:“我也觉得打击乐很好,我也很喜欢,它也有它的魅力,但是它不是我的终极职业理想。”随后,范妮补充道,指挥或许也不是自己的最终目标,她想尝试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尝试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她说,有一些事情是自己做不了的,比如说作曲,她说自己不是创作型和创造力的人,“对乐队熟悉,我可以去解读作品,假如说让我从无到有创造一个东西,我可能做不到。”范妮说,自己的兴趣很广泛,当初假如不去学指挥的话,她可能做学别的,比如说文学和电影。
做人不能什么都想要
范妮的家人和朋友对于后来成为指挥家的她的期待是,既能当打击乐家,也能做一名指挥家,这样有两条路可以走。但是范妮对父母说了一句话:“做人不能什么都想要。”所以,她说自己必须放弃一样,不可能两样都好,要想其中一个做得好,就必须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上面,所以学指挥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为了指挥会放弃更多打击乐的时间,但是指挥这个职业也不一定能走到什么地方,自己的未来是一种很OPEN的状态。“从台前转到幕后也没有不好,做指挥其实就是杂家,一个比较精的杂家,什么都比较精。就算有一天不干指挥了,以我对音乐的了解,我自己本身满足于对音乐的了解和追求,我就觉得挺好,但不一定要怎么样。”

有句老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范妮并不是一个凭着兴趣做事的人。就比如说,当初的她为什么专门去学了指挥专业,“我要是真想着做什么事情,就必须从根儿上去了解它,而拿自己的兴趣跟别人专业比是远远比不了的,所以必须要去学,必须了解到它最深层次的东西才行。” 也有人问范妮,作为一个指挥要具备什么必要的条件?她说:“这没法总结,作为指挥家学识广博,这毋庸置疑。有人说指挥要对生活热爱,我说不光是做指挥家,就是做一个人他都应该热爱生活。如果非问我,让我说一个词,那就是执念。不管我干什么,这种执念就是追求。有人问我追求什么?我说我想要追求一切的东西,只有有这个执念,才可以走到最后。”范妮说:“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但是自己必须要尝试其他的可能。”范妮认为,她现在的状态并非是一个结果,自己只是在路上,“谁还知道后十年是怎么样的?没有人知道!”按照范妮的说法,未来音乐界有可能会少了一位出色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但有可能在另一个领域里出现一个同样出色的范妮,范妮笑着打趣说:“也许吧,比如餐厅老板。”
作者 张学军 中华网加拿大频道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