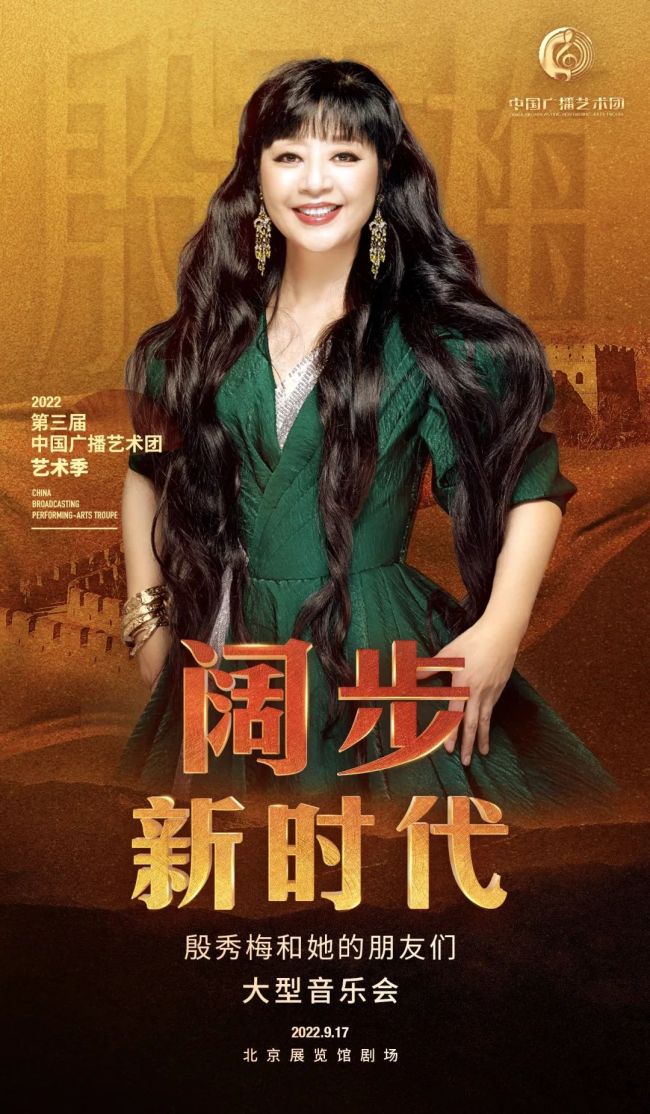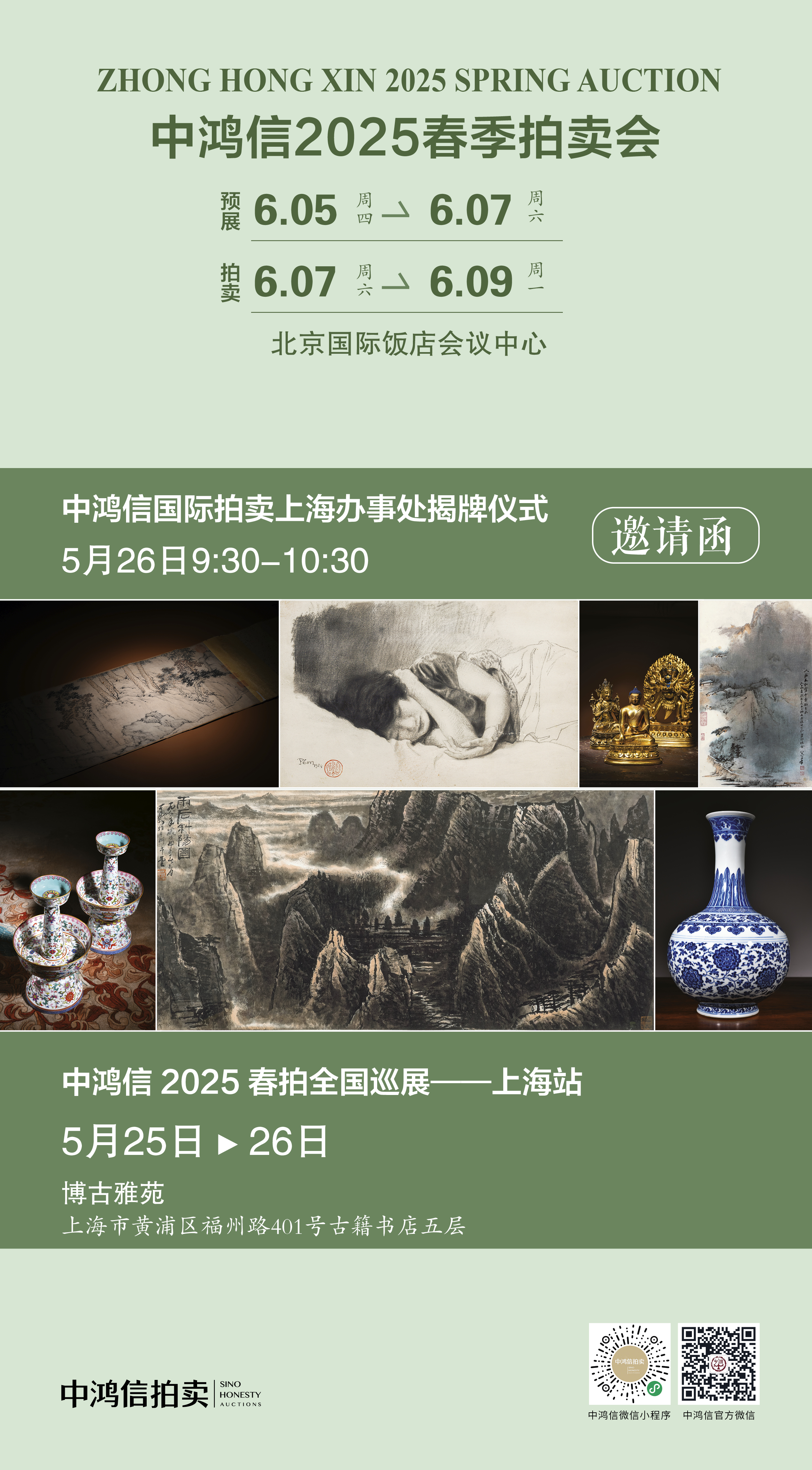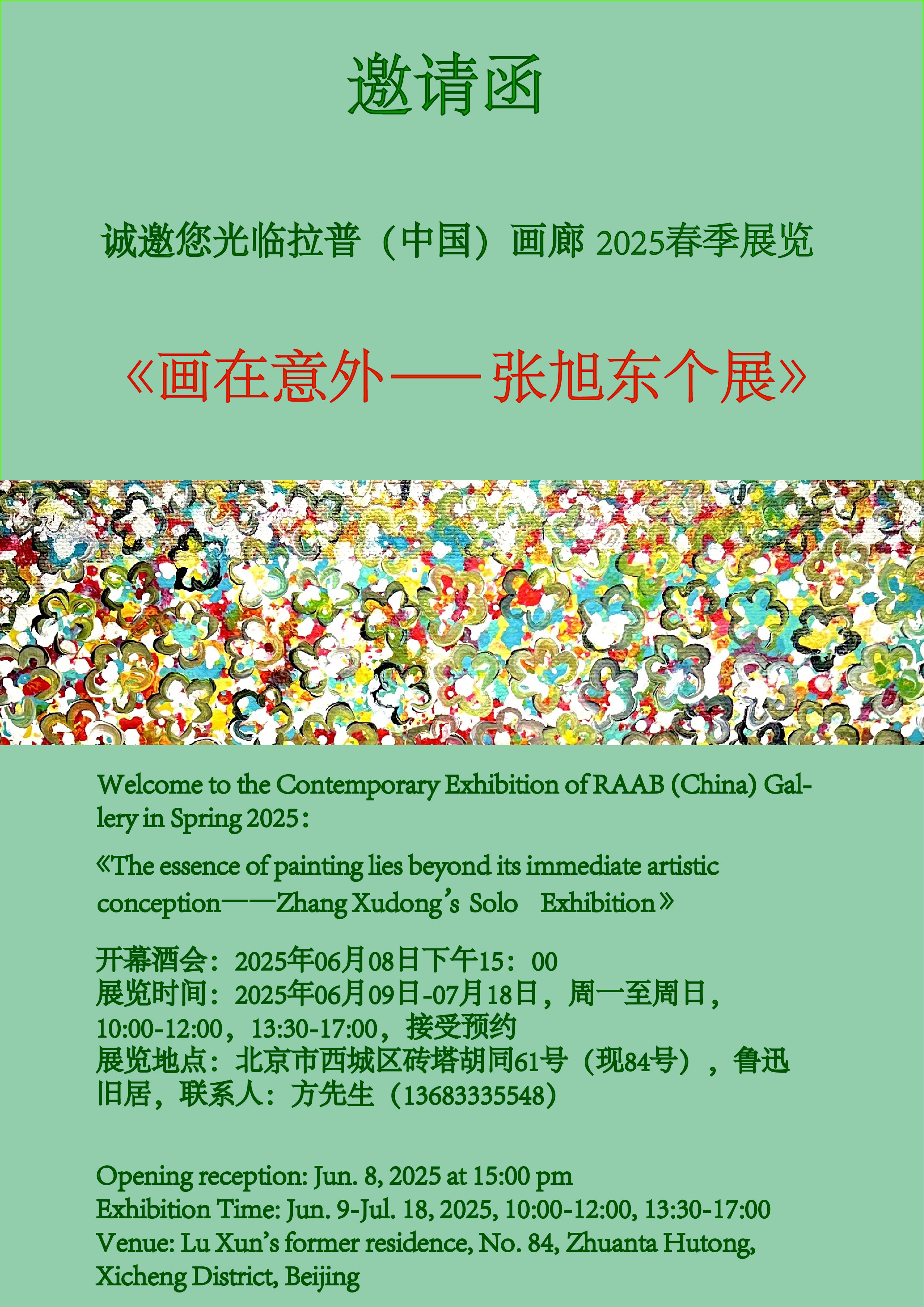音乐人小河:即兴,从严肃到“不严肃”的回归
舞蹈家和音乐家,二者在即兴当中的默契是心照不宣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是给对方更多的惊喜,或者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这样的感觉才能推动作品的发展。如果大部分时间彼此感到很糟糕或者不舒服,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往前推动的。
大概是2004年或者2005年,我就开始玩儿即兴了,一直到现在快20年了。即兴其实是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也不会说有什么特别激动的,更多的是平静。恰恰是这个平静的状态,才可能让你更清醒的看见当下应该怎么做。
陶身体的作品没有太多的指向性,比如他的数位系列,没有太多的情感和叙事的指向性,所以它让观众的参与度很高,更别提现在的即兴了,这是在必须有观众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作品。它没有与观众直接的比如语言声音身体上的互动,但它一定是让观众的意识和思维最大参与也是最大需求的作品。如果你想从这里看到你想要的故事,那你的参与度就不高了。但如果你放松下来,让声音在你的耳边展开,让肢体在你的眼前展开,然后让你的思维跟着他们游走,你的思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从严肃到“不严肃”的回归挺重要的,这个回归就证明我们的认知有变化,这种认知的迭代挺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从严肃到带引号的“不严肃”,我觉得是对未来的一个铺垫,未来可能会做更多更不一样的作品。

07小众艺术不需要破圈
现在做什事情都希望破圈,但我觉得破圈是在这个时代你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焦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流量,就是要火,火了之后就带来效益。但是纯艺术恰恰不需要这样,不需要破圈,你本就是小众的东西,越纯艺术越小众,你干嘛要破圈啊。反过来,你越珍贵,反而能破圈,这是跟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再说了,你又不是一个产品一个明星,破啥圈啊?我觉得破圈这个概念对于纯艺术家来说,是特别特别需要谨慎的。没有意义,比如说你赚点流量赚点钱,但这些跟你做的纯艺术有啥关系?艺术是很神圣的,纯艺术家就像修行者,他与这个世界要有出离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更看清人间烟火,而不为人间烟火所动。
破圈的概念误导了很多做艺术的人,好像所有做艺术的人都要火,做什么艺术都想火,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带给人的一个焦虑。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否则你就失去了阵营,你去破圈有流量了,你就不是艺术家了,就这么简单。
关键是艺术家本人,你到底是想火还是想做距离你的精神最接近的那个东西,你自己要清楚。如果你一直想做能火的事儿,火了以后又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千万不能一直想做纯艺术,但最终却总是抱怨自己没火。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生态,如果你是一个能引领人类精神趋向的艺术工作者,那你一定是要有失去的东西,你就不可能具有大市场,你一定要清楚自己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这个很重要。

08小众艺术不应当靠粉丝供养艺术家
去靠收割粉丝来供养艺术家,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粉丝这个概念是主流文化流行产业的一个概念,小众粉丝量本来就小,由他们去供养艺术家不现实。
艺术家和受众二者之间的平台是美术馆以及演出行业里的剧院甚至包括媒体。小众的艺术家,他的受众没办法供养他,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又能坚持做他的事情,这恰恰是他珍贵的所在。这样的艺术往往是引领人类精神层面趋向的工作,这部分工作最好是由国家和政府去支持。这几年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互联网让一些小众的艺术可以生存,这也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些类似剧院或者美术机构的平台给他们生存的信心和空间。当然,作为实体的美术馆或者剧院,可以带动大众审美提高的功能,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艺术家。
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纯艺术家和艺术就像动物的触角,它是伸在最前面的,它是探求人类这个大动物的未来的趋向和可能的边界。触角后面就有一些吞食和消化事物的入口,这就是诸如美术馆和剧院这样的平台和机构,吞食进去之后还有消化他们的胃,而这个胃就是大众,胃里面有他们需要的各种营养。作为剧院应该多采集不同的艺术品种去投喂观众,不能偏食,偏食就缺营养。前卫的、有票房的、大众小众都应当有他们存在的必要,不一定每场演出都能赚,但可以用赚到的钱填补一些小众艺术,我觉得这其实才是更健康的生态。
撰稿张学军 摄影范西